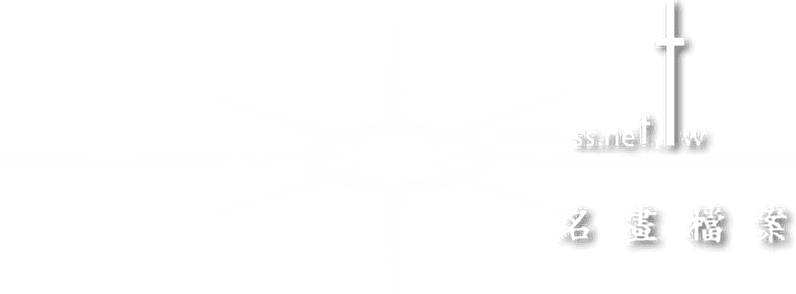在樹低下.一個女子嚮一名士兵彎下了腰。士兵的劍放在自己旁邊.他的一只手放在盾牌上.頭盔也在附近.就在畫的角落裏。女子跪下來.她的手放在年青年人的手上。看不清她是否真的碰觸到了。我們能感覺到:她很怕驚醒他.同時又在他不知道的情況下看著他的面容。就算女子溫柔的姿勢不足以證明.從她觀看士兵的方式也能明白看出:她對士兵表現出無比真實的溫柔。這真是個非常特別的時刻。然而.年輕女子另一只手裏拿著一把匕首.這破壞了我們的最初印象。故事現在變得複雜。一個長翅膀的小孩子.正是丘比特.愛的化身.他使出所有力氣.扒住女子的臂膀.很明顯.他想阻止女子使用匕首。從他表情的緊張程度判斷.他不太容易達成目標。這故事的背景是在十字軍東征時期。薩拉森女術士阿米達下定決心要殺死裏納爾多.一個基督騎士。複仇怒火燃燒字著她.女術士准備要發出致命一刺。她慢慢接近騎士.沒有發出一絲聲音。從她所處的位置.一切將會很快結束.輕而易舉。但那麽做就太簡單了。因此.丘比特介入了.愛神喜歡搞亂問題.把問題弄複雜.讓每個人都受點兒傷害。他在女子心中激起強烈愛意.現在.女術士放棄了想要殺死騎士的計劃。她本來是要置他于死地.但現在她卻感到某種欲望.想要去撫摸他的頭發。女術士不知道發生了什麽。神話似乎與現實相距甚遠.對於不熟悉古典神話的人來說.描繪它們的畫作無法從中感受到多少東西.很難對它們産生興趣.如果畫中人物像裏納爾多和阿米達這樣離我們那麽遙遠.就更是如此。不過.也根本沒有必要去深入研究塔索 1581 年的著作《耶路撒冷的解放》.不用知道每一個英雄的曆險故事.我們同樣可以了解他們的本質.他們那種愛恨交織、而又不會沖動的、詭異的混合情感。普桑是理性時代真正的聲音.他盡心盡力.保證自己的畫作能夠清晰明白。他選擇這種情感上的矛盾心態作爲描繪主題的基礎.更注重評論故事背後的含義.而不僅是畫出顯而易見的方面。他在阿米達身後畫出一棵樹。也許.那只不過是一種簡單的場景裝飾.但是它的樹幹同樣擋住了我們的視綫.說明這是一條她將要跨越的綫.一個門檻.是她將要越過的某條邊界的標志。同樣有意義的.是我們在裏納爾多背後看到的兩棵樹。在人物的軸綫上.在他頭頂.兩根樹幹一起生長、上升:阿米達將要碰到裏納爾多的時候.她發現了潛在的二元性。他既是她的敵人.也是她的愛人。真實的現實不再黑白分明。現在.她被兩種沖突的感情折磨:殺戮的欲望.以及突然間對于這陌生人全新的情感。在普桑其他作品中.他借助于古典戲劇面具中明顯而又豐富的面部表情。但在這裏沒有。阿米達的形象純潔.她微微張開的雙唇以最簡單的形式.傳遞出她的美麗和誘惑力.表現出她自己剛剛被人發現的單純.而她.作爲女術士.發現自己成爲另一個人的魔法的奴役。事情在發生時.仿佛阿米達的心態沒有受到影響.她也沒有必要表現出影響到她的感情波動:正如我們所見.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麽了。她被未名的感情震動.這感情目前還沒有被她明確認知。她的身體已經意識到了發生的一切。結果.她的身體.而不是她的臉.反映出她的感情.如同言語一般.明明白白說明它們的進展。她的右臂.握著匕首的右臂.沐浴在一道光中.展現出它的力量。蔓延胸膛的陰影.從她有力的肩膀直到她的手。丘比特爲了不讓她動手.必須用盡所有力氣抓住她。她背後的衣服像浪濤般翻滾.充分表明她原本要用的力氣。她自己的力量毋庸置疑。但激情的消耗如其産生那麽快。阿米達的另一條胳膊伸出陰影外.形成溫柔曲綫.在一小片光池中.她的手彎在裏納爾多手上。風景的綫條與女術士映襯。畫面左邊的山黑暗緊湊.但它勻稱地緩緩下降.地平綫也就慢慢下沈.就像年輕女子充滿愛的姿勢。裝飾士兵頭盔的羽毛延續了綫條的溫柔弧綫.如同一個優雅的右括號.慢慢下降。世界正在配合阿米達的情感。也許.這次純然優雅的相遇.能讓她發現自己與整個自然相一致。這幅畫揭示了一種名副其實的變形。我們看到阿米達在變。突如其來的感情顛覆了她.導致這次改變.她也意識到生命的悅動。包裹著她的藍色和白色衣衫.讓步于紅色.那本可能是裏納爾多的血.但現在.這是占據了她的激情。普桑描繪出女術士的溫柔情感、她發現這些情感的時刻.還有這些情感在她內心開放的時刻。這種溫柔變成某種教導力量.這溫柔爲畫面創建出空間.畫家也爲溫柔賦予了結構。魔女阿米達將要造出一座魔法宮殿.用來容納她的愛人。在男人之上.女人的臂膀已經形成一個拱.這是一個庇護所。